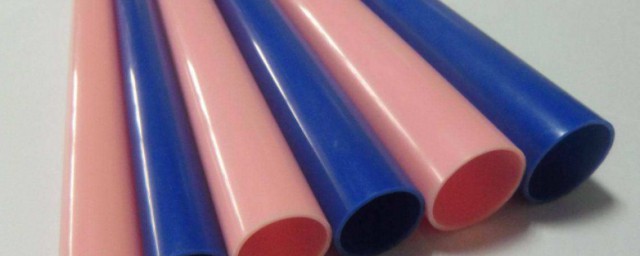1、原文:
一聲深沉的、驕傲的嗥叫,從一個山崖回響到另一個山崖,蕩漾在山谷中,漸漸地消失在漆黑的夜色裡。這是一種不馴服的、對抗性的悲鳴,和對世界上一切苦難的蔑視情感的迸發。
每一種活著的東西(大概還有很多死瞭的東西),都會留意這聲呼喚。對鹿來說,它是死亡的警告;對松林來說,它是半夜裡在雪地上混戰和流血的預言;對郊狼來說,是就要來臨的拾遺的允諾;對牧牛人來說,是銀行裡赤字的壞兆頭(指入不敷出);對獵人來說,是狼牙抵制彈丸的挑戰。然而,在這些明顯的、直接的希望和恐懼之後,還隱藏著更加深刻的含義,這個含義隻有這座山自己才知道。隻有這座山長久地存在著,從而能夠客觀地去聽取一隻狼的嗥叫。
不過,那些不能辨別其隱藏的含義的人也都知道這聲呼喚的存在,因為在所有有狼的地區都能感到它,而且,正是它把有狼的地方與其他地方區別開來的。它使那些在夜裡聽到狼叫,白天去察看狼的足跡的人毛骨悚然。即使看不到狼的蹤跡,也聽不到它的聲音,它也是暗含在許多小小的事件中的:深夜裡一匹馱馬的嘶鳴,滾動的巖石的嘎啦聲,逃跑的鹿的砰砰聲,雲杉下道路的陰影。隻有不堪教育的初學者才感覺不到狼是否存在,和認識不到山對狼有一種秘密的看法這一事實。
我自己對這一點的認識,是自我看見一隻狼死去的那一天開始的。當時我們正在一個高高的峭壁上吃午飯。峭壁下面,一條湍急的河蜿蜒流過。我們看見一隻雌鹿──當時我們是這樣認為──正在涉過這條急流,它的胸部淹沒在白色的水中。當它爬上岸朝向我們,並搖晃著它的尾巴時,我們才發覺我們錯瞭:這是一隻狼。另外還有六隻顯然是正在發育的小狼也從柳樹叢中跑瞭出來,它們喜氣洋洋地搖著尾巴,嬉戲著攪在一起。它們確確實實是一群就在我們的峭壁之下的空地上蠕動和互相碰撞著的狼。
在那個年代裡,我們還從未聽說過會放過打死一隻狼的機會那種事。在一秒鐘之內,我們就把槍彈上瞭膛,而且興奮的程度高於準確:怎樣往一個陡峭的山坡下瞄準,總是不大清楚的。當我們的來復槍膛空瞭時,那隻狼已經倒瞭下來,一隻小狼正拖著一條腿,進入到那無動於衷的靜靜的巖石中去。
當我們到達那隻老狼的所在時,正好看見在它眼中閃爍著的、令人難受的、垂死時的綠光。這時,我察覺到,而且以後一直是這樣想,在這雙眼睛裡,有某種對我來說是新的東西,是某種隻有它和這座山才瞭解的東西。當時我很年輕,而且正是不動扳機就感到手癢的時期。那時,我總是認為,狼越少,鹿就越多,因此,沒有狼的地方就意味著是獵人的天堂。但是,在看到這垂死的綠光時,我感到,無論是狼,或是山,都不會同意這種觀點。
自那以後,我親眼看見一個州接一個州地消滅瞭它們所有的狼。我看見過許多剛剛失去瞭狼的山的樣子,看見南面的山坡由於新出現的彎彎曲曲的鹿徑而變得皺皺巴巴。我看見所有可吃的灌木和樹苗都被吃掉,先變成無用的東西,然後則死去。我看見每一棵可吃的、失去瞭葉子的樹隻有鞍角那麼高。這樣一座山看起來就好像什麼人給瞭上帝一把大剪刀,並禁止瞭所有其他的活動。結果,那原來渴望著食物的鹿群的餓殍,和死去的艾蒿叢一起變成瞭白色,或者就在高於鹿頭的部分還留有葉子的刺柏下腐爛掉。這些鹿是因其數目太多而死去的。
我現在想,正像當初鹿群在對狼的極度恐懼中生活著那樣,那一座山將要在對它的鹿的極度恐懼中生活。而且,大概就比較充分的理由來說,當一隻被狼拖去的公鹿在兩年或三年就可得到補替時,一片被太多的鹿拖疲憊瞭的草原,可能在幾十年裡都得不到復原。
牛群也是如此,清除瞭其牧場上的狼的牧牛人並未意識到,他取代瞭狼用以調整牛群數目以適應其牧場的工作。他不知道像山那樣來思考。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瞭塵暴,河水把未來沖刷到大海去。
我們大傢都在為安全、繁榮、舒適、長壽和平靜而奮鬥著。鹿用輕快的四肢奮鬥著,牧牛人用套圈和毒藥奮鬥著,政治傢用筆,而我們大傢則用機器、選票和美金。所有這一切帶來的都是同一種東西:我們這一時代的和平。用這一點去衡量成就,全部是很好的,而且大概也是客觀的思考所不可缺少的,不過,太多的安全似乎產生的僅僅是長遠的危險。也許,這也就是梭羅的名言潛在的含義。這個世界的啟示在荒野。大概,這也是狼的嗥叫中隱藏的內涵,它已被群山所理解,卻還極少為人類所領悟。
2、《像山那樣思考》是美國作傢、“近代環保之父”奧爾多·利奧波德創作的一則隨筆,揭示瞭在人類的愚蠢下種種短視行為背後隱藏的巨大的自然破壞和生存危機,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