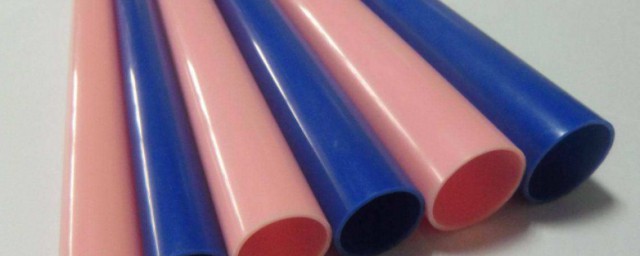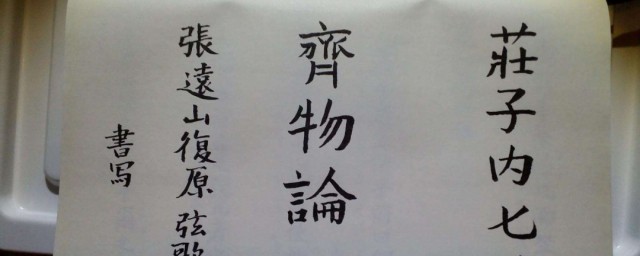
1、原文
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顏成子遊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機者,非昔之隱機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不聞天籟夫!”
子遊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陵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窪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於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子遊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鬥。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蜇,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2、翻譯
南郭子綦靠幾靜坐,仰面朝天緩緩地吐氣,茫然若失,就像魂魄離開瞭軀體。南郭子綦的學生顏成子遊見狀馬上前來侍候,問南郭子綦說:“您剛才是處於一種什麼樣的境界呢?一個人的肢體形貌在打坐時固然可以使它像枯槁之木一樣毫無生氣,難道一個人的心神在打坐時也可以使它像死灰一樣毫無生氣嗎?您在今天所表現出來的安穩境界,跟以前的安穩境界絕對不一樣。”南郭子綦回答說:“偃,你問此事,不是問得很好嗎?今天我遺忘瞭形體之我,你知道這一點嗎?你隻聽到人吹簫管發出的聲音,而沒聽聽風吹眾竅所發出的聲音,你隻聽到風吹眾竅所發出的聲音,而沒有聽到天地間萬物的自鳴之聲!”
子遊說:“能不能問一問大地的聲音與天的聲音是怎麼回事呢?”南郭子綦回答說:“那個地籟就是無邊無際的造物之作用所發出的能量之氣息啊,發出來之後就被叫作風。這種能量要麼就是內在蘊含著不發出來,一旦發出來就會萬竅怒號,難道你耳邊就沒有聽到過這種‘呼呼’的風聲嗎!山林的險峻、大樹周身的竅穴,有的形狀像鼻子,有的形狀像張開的嘴,有的形狀像耳朵,有的形狀”像扁長的發簪,有的形狀像凸出來的圈筒,有的形狀像凹下去的淺坑,有的淺一些,有的深一些;於是所發的聲響就有的快促,有的像響箭,有的刺耳,有的發自往裡吸,有的發自往外出,有的像嚎哭聲,有的像狗叫,有的像悲哀聲。能量流的運動原本就很舒緩動聽,怪就怪哉隨著各種物體所發出的眾口亂叫而嘈雜瞭;當徐徐之風時萬物就會輕微地唱和,當風大時萬物就會大點兒地唱和,當勁風厲厲時反而所有能發響者皆欲發而無聲瞭,難道你沒有從風響的音調中聽出來各種聲響的發聲原因、從風的響聲上聽出其後面的那個不發聲的東西嗎?”
子遊又問:“大地的本意可以借助萬物之竅所發出的唱和聲中表達出來,人所的本意也可以從清悠、消沉、諧美的各種絲竹的或條暢或激昂的聲中表達出來,那麼天的本意是怎麼表達出來的呢?”南郭子綦說:“所謂天籟的音響萬變,而又能使其自行息止,這完全都是出於自然,有什麼東西主使著它呢?”
大智者看上去顯得非常廣博,小智者卻十分瑣細;高論者盛氣凌人,爭論者小辯不休。辯士睡時,精神與夢境交錯在一起,醒後疲於與外物接觸糾纏。每天與外物相接,其心有如經歷瞭一場又一場的戰鬥一樣疲憊。有的心機柔奸,有的善設陷阱,有的潛機不露。小的懼怕表現為憂懼不安,大的懼怕表現為驚恐失神。三災八難的降臨就像箭在弦上一樣地隨時而發,這全是由於行為人的心機所伺機行是非之行徑所造成的;三災八難的不降臨也可以像發願一樣的通過履踐其願誓而消失,那就要看行為人是否踐履自己的願誓而堅持無思無為的行徑來決定瞭。神情衰沮就像秋風冬雪肅殺萬木一樣無情,這就說明道心逍遙之本性的消亡是漸進的過程;如果行為人沉迷於自己之心機的經營裡而不醒悟的話,也就很難再回到那個逍遙的本性去瞭。然而行為人對恢復道心的修行卻厭惡得像自行封閉起來的蠶子一樣的聽不進去,這就說明行為人的執著意識的積習太嚴重瞭;像這樣的幾乎等於死亡的心,實在是沒法使它再恢復生氣。所謂的喜怒哀樂,都是認取瞭事物對自己所引發的感受而逐步形成多憂懼的意識,正在這個意識之執著的支配下才形成瞭輕狂而放任的或喜或怒或哀或樂的情緒瞭。喜怒哀樂發出來之後就過去瞭,接著而來的就是又孕育出瞭無明之煩惱,如此的一天到晚的不是喜樂就是煩惱的交替著出現在眼前,而從來不知道它們是怎麼產生的。不可救藥啊,不可救藥!一天到晚地如此活著,三災八難也就由此產生瞭啊!
如果沒有瞭我之內外的任何對立面的觀念也就沒有我的觀念瞭,如果沒有瞭我的觀念也就沒有瞭博取之心瞭,如此也就基本上接近於那個道心的行徑瞭,然而卻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在支配著這個道心的行徑。好像其中有一個迫使萬物循勢而動的主宰在,然而偏偏找不到那個主宰的跡象在什麼地方,當你恢復瞭道心之後就會徹底明瞭那個迫使萬物循勢而動的主宰瞭,但它卻又沒有一個具體的形狀可見,它僅僅是道心的廣大無緣之悲性而沒有具體形狀而已。一個人身上有百骸、九竅、六臟,當這些臟器都完備瞭之後才能決定一個人的生存,那麼你認為哪一個臟器最重要而倍加愛護呢?還不是都喜歡而都倍加愛護嗎?這個問題的背後豈不牽扯到一個“私我”的觀念瞭嗎?如果有一個“私我”之觀念的話,那麼各臟器豈不就成瞭分別為“私我”提供專職服務的臣下與妻妾瞭嗎?這種勢必缺乏協調性的臣下與妻妾豈不就不足以擔當全面治理整個機體的重任瞭嗎?難道它們是逐個輪流著擔當君的職責而協調各位臣妾的工作嗎?這就證明裡面有一個真正的主宰在後面起著決定作用嗎?如果實證到瞭那個廣大無緣之慈悲性的道心原來是沒有具體形狀可得的時候,那時候就會明白這個真宰的作用無論怎麼做都既不會益於也不會損於那個真宰者的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凈性瞭。然而自從那個人人都有的真主秉承瞭執著之意識以投胎成人之後,還沒有到該死的壽數時就在哪裡等著壽盡的一天瞭,這是因為內外界事物所誘發的愛、惡、欲、的心行在相爭鬥以至於相消耗的緣故;明明知道生命的壽終就像飛馳一樣,但卻不知道如何止住這種邁向壽終的步伐,對於自許聰明的人們來說難道不是一種悲哀嗎!隻知道一輩子地役使自己的心身去赴愛、惡、欲的勞役但對於恢復道心卻毫無一點兒進展,整天精神不振地疲於勞役但卻不知道究竟是為瞭什麼,對於自許聰明的人們來說難道不是一種痛心嗎!即使能夠達到人們所說的千萬歲的長生不老,對於道心的恢復又有什麼益處呢?即使其形體逐漸衰敗枯萎,也隻是其執著心使其具有瞭這種變化而已,對於那個真宰的不生不死、不增不減、不垢不凈性而言怎能不是最大的痛心呢!人生在世,本來就如此糊塗嗎?